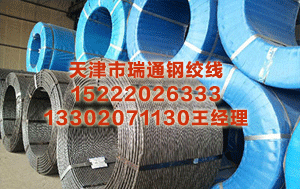仙桃预应力钢绞线价格 戴笠子被处决, 两年后消息传到台湾, 蒋介石: 他的子孙全接过来

声明:本文基于历史事件进行文学化改编创作仙桃预应力钢绞线价格,部分情节、对话及细节为艺术加工,旨在呈现历史故事的戏剧张力,不代表历史对真实。请读者理看待,勿将虚构情节与历史事实混淆。
1953年的中国台北,天像是漏了一样,连着下了半个月的雨。
阳明山脚下的士林官邸,被笼罩在一层灰蒙蒙的雾气里。这里的气氛比外面的天气还要阴沉。那些穿梭在回廊里的侍卫和秘书,走路都踮着脚,生怕弄出一点动静,惊扰了官邸主人此刻并不平静的心情。
在二楼那间宽大的办公室里,蒋介石穿着一件半旧的长袍,手里拄着拐杖,站在窗前看了很久的雨。他的背影显得有些佝偻,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萧索。
办公桌上,放着一张来自香港的加急电报。那张薄薄的纸片,已经被他捏得满是褶皱。
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站在门口,低着头,连大气都不敢喘。他太熟悉蒋介石的脾气了,这种死一般的沉默,往往是雷霆震怒的前兆。
电报上的内容很简单,每一个字却都像钉子一样扎人:戴笠唯一的儿子戴藏宜,已经于两年前的1951年,在浙江江山老被公开枪决了。
这个消息整整晚了两年才传到台北。
蒋介石转过身,脸铁青。他看着毛人凤,声音沙哑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狠劲:“雨农为党国干了一辈子的脏活,死了不到七年,连个后都没保住?你们保密局是干什么吃的?”
毛人凤扑通一声跪在地上,额头贴着地毯:“校长,卑职无能!”
蒋介石重重地顿了一下拐杖:“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不管花多少钱,死多少人!雨农留下的那几个子孙,须全部给我毫发无损地接回台湾!少一个,你也别回来了!”
这是一道死命令。但在1953年,想要从严密封锁的上海把人弄出来,这道命令几乎就是让特工去送死。
01
1953年的上海,初春的寒气还透着骨头缝里的冷。
在静安区一条不见底的弄堂里,天还没亮,倒夜壶的声音就响成了一片。这里的房子老旧,木板墙薄得像纸,隔壁两口子吵架,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郑锡英缩在阁楼的破棉被里,听着楼下弄堂口传来的脚步声,浑身都在发抖。那是街道办事处的大妈带着户籍警在巡查。
自从三年前丈夫戴藏宜在江山老被抓走后,郑锡英觉得自己的天塌了。
她带着三个儿子一路逃难,后像阴沟里的老鼠一样躲进了上海这个大城市。她不敢用真名,不敢提江山,更不敢提那个曾经让人闻风丧胆的公公戴笠。
现在的她,只是一个靠糊火柴盒度日的寡妇。
“娘,我饿。”
被窝里,二儿子戴以宏迷迷糊糊地哼了一声。
郑锡英赶紧捂住儿子的嘴,压低声音说:“嘘!别出声!等警察叔叔走了再起来。”
她看着身边的三个孩子。大儿子戴以宽已经懂事了,睁着眼睛盯着黑乎乎的屋顶,眼神里有着不属于这个年纪的惊恐;小的儿子戴以昶还不到十岁,睡得正沉。
郑锡英心里苦啊。她本是江山的大户人小姐,嫁入戴后也是呼奴唤婢的少奶奶。谁能想到,短短几年,沧海桑田,如今为了活命,连个囫囵觉都不敢睡。
她摸了摸藏在枕头芯子里的两根小黄鱼,那是戴笠留下的后一点底,也是这三个孩子的保命钱。她想去台北,可看着满大街带着红袖章的巡逻队,她觉得那条海峡比登天还难跨越。
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台北保密局密室里,烟雾缭绕。
毛人凤坐在皮椅上,面前摆着一份厚厚的人员档案。他在挑人。
这次任务是“虎口拔牙”,去的人不仅要忠诚,还得是个“老上海”,既要懂黑话,又要能在三教九流里混得开,重要的是,得不怕死。
“局长,您看这个黄铎怎么样?”旁边的官递过来一张照片。
照片上的人长着一张扔进人堆里就找不见的大众脸,眼神却透着股狠劲。
“黄铎……”毛人凤眯起眼睛回忆了一下,“是当年跟过雨农的老人吧?我记得他在上海青帮里都有过香堂?”
“是。这人是个狼,早年间在上海潜伏过五年,熟悉那边的路子。而且他枪法好,脑子活,关键的是,他欠戴先生一条命。”
毛人凤把烟头狠狠按灭在烟灰缸里:“就他了。马上派飞机把他送到舟山群岛,然后找走私船让他潜入上海。告诉他,这是老头子亲自下的令,办成了,回来升官发财;办不成,让他自己找块地把自己埋了,别连累眷。”
当天晚上,黄铎就被带到了毛人凤面前。
这个汉子听完任务,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要了一根烟,抽了一半才说:“局长,我去。但我有个条件,要是我折在那边了,我老娘和老婆,局里得管一辈子。”
毛人凤拍了拍他的肩膀:“你放心,只要你去了,不管成不成,你全就是党国的功臣。”
黄铎点点头,把剩下半截烟抽完,起身敬了个礼,转身走进了茫茫夜。他知道,这一去,九死一生。
几天后,一艘挂着捕鱼旗号的破旧机帆船,趁着夜,悄悄停靠在了上海吴淞口外的一片芦苇荡里。
黄铎换了一身打满补丁的粗布短褂,脚上踩着一双烂布鞋,背着个破麻袋,看上去就像个刚从苏北来上海讨生活的苦力。
他跳下船,踩着泥泞的江滩,一步步走向那个霓虹灯闪烁却又危机四伏的上海滩。他要在几百万人口里,找到郑锡英母子,还得把他们全须全尾地带出来。
02
进了上海,黄铎没有急着去找人。他像个真正的流浪汉一样,在十六铺码头扛了两天大包,混熟了地头,也摸清了现在的盘查规律。
现在的上海,跟几年前不一样了。派出所管得严,尤其是对外来人口,那眼神利得像刀子。
三天晚上,黄铎来到了法租界旧区的一茶馆。他找了个角落坐下,要了一壶便宜的碎,眼睛却死死盯着门口。
不一会儿,一个穿着中山装、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这人叫陆秉章,以前是军统的外围,解放后因为没做什么大恶,加上业务熟练,被留用在了上海市公安局户籍科。
这就是黄铎此行关键的棋子。
陆秉章刚坐下,黄铎就悄无声息地坐在了他对面。
“借个火。”黄铎压低帽檐,手里捏着一根没点着的烟。
陆秉章一抬头,看清了黄铎那双眼睛,手里的茶杯差点吓得掉在地上。他当然认识这双眼睛,当年在军统特训班,这双眼睛让他做了好几天噩梦。
“你……你怎么来了?”陆秉章的声音都在发抖,左右看了看,压低声音,“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不要命了?”
“老陆,别来无恙啊。”黄铎冷笑了一声,“听说你现在混得不错,都当上警察了?”
“混口饭吃……混口饭吃……”陆秉章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黄兄,有什么事你直说,说完赶紧走。”
黄铎从怀里掏出一张照片,那是戴笠的遗照,背面写着几个字:接人,急。
“老头子发话了,要接戴先生的儿媳妇和孙子去台湾。”黄铎盯着陆秉章的眼睛,“这事儿,得靠你。”
陆秉章一听,脸瞬间煞白:“这不可能!现在出境查得多严你不知道?没有正当理由,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更何况是戴的人?那是监控对象!”
“所以我才来找你。”黄铎从桌下递过去一根金条,硬塞进陆秉章的手里,“我们需要一套合法的身份,还有出境证。理由我都想好了,就说是去香港探亲,现在的政策,去香港虽然难,但只要手续齐全,还是有口子的。”
陆秉章手里捏着那根金条,觉得烫手得要命。他想拒,可看着黄铎腰间鼓起的那一块,他知道自己没得选。这是军统的法,不答应,今晚就得死。
“几个人?”陆秉章咬着牙问。
“郑锡英,加上三个孩子,四个。”黄铎伸出四根手指。
“四个……”陆秉章盘算着,“那是孤儿寡母,太扎眼了。现在的边检不是傻子,一个年轻女人带三个男孩去香港,肯定会被盘问丈夫去哪了。如果没有男人,这戏演不下去。”
黄铎沉默了一秒:“我来演这个丈夫。”
陆秉章瞪大了眼睛:“你?你的身份经得起查吗?”
“所以我需要你给我造一套假档案。”黄铎语气冰冷,“就说是广东来的商人,在上海做生意亏了,带老婆孩子回香港投奔亲戚。这套词儿,我熟。”
“那就是五个人。”陆秉章的眉头皱成了川字,“五套证件……还要在户籍底册上做手脚……这太难了。现在局里对空白的出境证管得跟子弹一样严,每一张都有编号。”
“那是你的事。”黄铎站起身,拍了拍陆秉章的肩膀,“三天后,还是这个时间,我来拿东西。老陆,想想你在台湾的老婆孩子,这一票干成了,你也跟我们一起走,去那边团聚。”
说完,黄铎消失在了夜里。
陆秉章瘫坐在椅子上,觉得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他知道,自己已经上了贼船,下不来了。
接下来的三天,陆秉章过得像在油锅里煎熬。
他利用值夜班的机会,偷偷潜入档案室。他的手抖得厉害,好几次差点把墨水瓶打翻。他翻出了几张作废重填的户籍底单,小心翼翼地修改着上面的名字和籍贯。
“沈凤英……”他给郑锡英起在这个假名。
“长子、次子、三子……”
然后是难的一步,偷空白的出境通行证。
那天中午,趁着科长去开会,保管员上厕所的空档,陆秉章溜到了保管柜前。他的心跳得快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他用备用钥匙打开了柜子,数了数里面的一沓证件。
他原本想拿五张。
可是当他的手伸进去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这一本新的证件薄,只剩下了后四张连号的。下一本锁在更里面的保险柜里仙桃预应力钢绞线价格,他没有钥匙。
如果强行撬锁,肯定会留下痕迹,明天一上班就会暴露。那时候,别说走人了,全城都会戒严抓人。
只有四张。
陆秉章站在柜子前,冷汗顺着鬓角流进了脖子里。
拿,还是不拿?
拿了,就只有四张票,五个人怎么分?
不拿,等到明天,黄铎那个煞星一定会杀了他。
远处传来了走廊里的脚步声,那是同事回来了。
陆秉章牙一咬,心一横,一把抓起那仅剩的四张通行证,揣进怀里,飞快地关上了柜门。
他回到座位上时,整个人像虚脱了一样。他摸着怀里那薄薄的四张纸,心里清楚,这不仅仅是四张纸,这是要命的阎王帖。
少了一张票,这就意味着,在即将到来的逃亡之夜,有一个人,注定要被抛弃。
03
三天后的夜里,上海下起了瓢泼大雨。
郑锡英在阁楼里焦急地走来走去。她已经接到了黄铎的通知,今晚就走。
三个孩子都穿上了厚的衣服,虽然外面套着破旧的罩衫,但里面其实穿了好几层。郑锡英把仅剩的金条和银元缝在孩子们的棉裤腰里,叮嘱他们无论如何不能脱裤子。
“娘,我们去哪儿啊?”小儿子戴以昶揉着惺忪的睡眼问。
“去见爷爷的朋友,去好地方,那里有白米饭吃,有糖吃。”郑锡英强忍着眼泪,挤出一个笑容。
大儿子戴以宽一直没说话,他紧紧攥着母亲的衣角,似乎预感到了什么。二儿子戴以宏则在旁边摆弄着一个破木头手枪,那是他在垃圾堆里捡来的宝贝。
“咚、咚、咚……”
门外传来了约定的敲门声。三长两短。
郑锡英的心猛地提到了嗓子眼。她一把拉开门,黄铎带着一身雨水闪了进来,后面跟着脸惨白的陆秉章。
“快!船在吴淞口等着,还有一个小时开船!”黄铎一边说,一边看向陆秉章,“东西呢?”
陆秉章颤巍巍地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了桌子上。
那里面是五个人这一生的希望。
郑锡英激动得手都在抖,她伸手去拿那个信封,嘴里念叨着:“谢天谢地,终于能走了,终于能走了……”
“慢着。”
陆秉章突然按住了信封,声音沙哑得像吞了炭,“老黄,嫂子……我有罪。”
黄铎眼神一凛,手立刻摸向了腰间:“怎么回事?证件有问题?”
“证件是真的。”陆秉章痛苦地闭上眼睛,“但是……只有四张。”
“什么?”
这声惊呼是郑锡英喊出来的。她虽然不懂特工那一套,但小学数学她是会的。
“我们……我们有五个人啊!”郑锡英指着自己和三个孩子,又指了指黄铎,“怎么只有四张?”
黄铎一把揪住陆秉章的领子,把他顶在墙上,眼睛红得像要吃人:“你玩我?少一张票,你让我们怎么过关?你想让我们死在关卡上吗?”
“我没办法啊!”陆秉章哭丧着脸,声音里带着望,“柜子里就剩这四张了!我要是去撬保险柜拿五张,当时就得露馅,大都得死!我只能拿这四张……我真的尽力了!”
黄铎松开了手,陆秉章顺着墙滑到了地上。
屋子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窗外的雨声显得格外刺耳,像是在给这间屋子里的望伴奏。
五个人,四张票。
这是一个无解的死局。
TA评选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百大球星(包括附加赛球队的球员):
消息人士说,以列情报和特勤局局长巴尔内亚25日在巴黎会见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和卡塔尔相穆罕默德后返回以列。三人在会议期间决定,钢绞线厂家将于下周根据埃及和卡塔尔的新提议开启谈判。另据以列瓦拉新闻网25日报道,以列一名官员在上述巴黎会议后表示,决定在下周恢复关于交换被扣押人员的谈判。
“能不能挤一挤?”郑锡英带着哭腔问,“以昶还小,能不能不占票?或者藏在行李里?”
“嫂子,你清醒一点!”黄铎低声吼道,“那是边防检查!是一个个对人头的!别说藏个人,就是多带个包都要查半天。少一张证,只要被查出来,立刻就会被当成特务抓起来,到时候谁都走不了!”
黄铎吸了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是这次行动的指挥,他须做决断。
“我不能留。”黄铎指着自己,“没有我这个‘丈夫’顶在前面应付盘查,你一个女人带孩子根本出不了上海,走到火车站就被扣了。我须走。”
郑锡英点点头,她知道黄铎说的是实话。
“嫂子你是孩子的妈,又是戴先生点名要接的人,你也须走。”黄铎继续分析,语气冷酷得像机器。
那么,剩下的两张票,只能给两个孩子。
也就是说,三个孩子里,须有一个留下来。
郑锡英觉得一阵天旋地转,差点晕过去。她扶着桌子,看着眼前的三个亲骨肉。
大儿子戴以宽,12岁,那是长房长孙,是戴的香火,按照老理儿,那是死也要保住的根。
小儿子戴以昶,才6岁,正是离不开娘的时候,留他在上海,跟让他死没什么区别。
郑锡英的目光,颤抖着,终落在了二儿子戴以宏的身上。
戴以宏今年8岁,不不矮,不胖不瘦。他手里还拿着那个破木头手枪,正仰着头,一脸懵懂地看着大人们,似乎不明白为什么气氛突然变得这么可怕。
“没时间了!”黄铎看了一眼手表,那滴答声像是催命的鼓点,“还有后十分钟,再不走,四张票作废,大一起死在这里!”
他一把抓起桌上的通行证,塞进郑锡英手里,然后猛地把两张儿童票拍在桌子上。
“嫂子,选吧!带谁走?留谁?”
这大概是世界上残忍的选择题。
郑锡英浑身都在哆嗦,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她慢慢地蹲下身,伸出双手,想要去抱所有的孩子,但手伸到一半,却僵在了空中。
她看向大儿子,大儿子往后缩了缩;她看向小儿子,小儿子死死抱着她的腿。
后,她看向了戴以宏。
“以宏……”郑锡英的声音听起来像是从胸腔里撕裂出来的。
戴以宏眨了眨眼睛,走过来,用那双脏兮兮的小手给母亲擦眼泪:“娘,你怎么哭了?是不是我要吃糖你不兴了?那我以后不吃了。”
这一句话,像刀子一样扎穿了郑锡英的心脏。她一把将二儿子搂进怀里,嚎啕大哭。
“娘对不起你……娘对不起你啊!”
哭声在狭窄的阁楼里回荡,连铁石心肠的黄铎都别过头去,不忍心看这一幕。
时间到了。
黄铎一把拉起郑锡英:“嫂子,走!”
郑锡英像疯了一样,在戴以宏的额头上狠狠亲了一口,然后把他到了陆秉章的怀里。
“老陆!求你了!”郑锡英跪在地上,把头磕得咚咚响,“帮我照顾他!只要我活着到了台湾,我一定想办法来接他!求你了!”
陆秉章也是泪流满面,死死抱住挣扎的戴以宏:“嫂子放心!只要我有一口吃的,就不让孩子饿着!”
“娘!娘!你要去哪?”戴以宏终于反应过来了,他拼命挣扎着,想要去追母亲,“我也要走!我也要坐大轮船!”
“以宏乖!娘去给你买好吃的,过几天就回来接你!”郑锡英一边流泪一边撒着这辈子痛心的谎。
“走!”
黄铎拉起郑锡英,带上大儿子和小儿子,头也不回地冲进了雨夜。
身后,阁楼的门重重关上。
门缝里,传出了戴以宏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娘——!别丢下我——!”
那哭声穿透了雨幕,像一只无形的手,死死抓着郑锡英的后背。她不敢回头,怕一回头,就再也迈不动步子了。
雨越下越大,仿佛要冲刷掉这个夜晚所有的罪恶与无奈。
04
逃亡的路,每一步都是踩在刀上。
黄铎带着母子三人,在风雨中狂奔到了吴淞口。那艘接应的货船早就等得不耐烦了,如果再晚十分钟,船老大就要起锚走人。
上了船,郑锡英瘫软在满是鱼腥味的货舱里,整个人像被抽走了魂魄。她怀里紧紧抱着小儿子,眼睛却直勾勾地盯着那个漆黑的船舱顶,耳边全是二儿子刚才那声凄厉的“娘”。
大儿子戴以宽缩在角落里,吓得一句话也不敢说。他知道,弟弟是为了让他们活,才被留下的。这种负罪感,哪怕是孩子,也觉得沉重得喘不过气。
船在海上颠簸了两天两夜,终于到了广州。
那时候没有直飞台湾的飞机,他们须先到广州,然后坐火车到圳,再偷渡去香港。这一路上,危险的就是广州火车站的检查。
广州火车站人山人海,到处都是背着大包小包的旅客,但也到处都是巡逻的战士。
黄铎换上了一身笔挺的西装,头发梳得油光锃亮,架着一金丝眼镜,活脱脱一个广东阔商的模样。郑锡英也换上了一件像样的旗袍,虽然脸苍白,但也尽量装出一阔太太的架势。
“记住了,我是做药材生意的,去香港收账,你是我的二房太太,这俩是我们的孩子。”黄铎低声嘱咐,“不管问什么,你就装头晕,不舒服,别说话,一切有我。”
到了检票口,几个战士正拿着画像在比对。郑锡英的心跳得像是要炸开一样,她死死抓着黄铎的胳膊,指甲都嵌进了他的肉里。
“证件。”一个年轻的战士拦住了他们,目光在郑锡英脸上停留了几秒。
黄铎一脸不耐烦地掏出那四张用命换来的通行证,嘴里操着一口流利的粤语抱怨道:“阿sir,快点啦!火车要开啦!我老婆晕车晕得厉害,再不上去要吐在这里啦!”
战士接过证件,仔细核对着上面的钢印和照片。那几秒钟,对郑锡英来说,比几年还要漫长。
突然,战士指着小儿子戴以昶问:“这孩子怎么一直低着头?”
郑锡英浑身一僵。
黄铎反应快,伸手就在戴以昶后脑勺上拍了一巴掌,骂道:“没出息的东西!看见叔叔害羞个什么劲!叫人!”
戴以昶被这一巴掌打懵了,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这一哭,反而打消了战士的疑虑。哪有特务带着这么熊的孩子的?
“行了行了,赶紧进去吧,别挡着后面的人。”战士挥挥手,把证件递了回来。
那一瞬间,郑锡英觉得自己的腿都是软的,几乎是被黄铎架着走过了检票口。
又是一路惊魂。
终于,在一个月黑风的夜晚,他们趴在圳河边的草丛里。对岸就是香港,那里灯火通明,仿佛是另一个世界。
“过去就是活路。”黄铎指着河对岸。
他们趟过冰冷的河水,那一刻,郑锡英回过头,望着北方那片漆黑的大陆。她知道,她的二儿子戴以宏,此刻就在那片黑暗的处,或许正在哭泣,或许正在挨饿。
“以宏,娘对不起你……”她在心里默默念着,泪水混合着河水流进嘴里,苦涩得让人望。
几天后,一架从香港起飞的机,降落在了台北松山机场。
机场上早就停满了黑的轿车。保密局的官们列队迎接。当舱门打开,郑锡英牵着两个孩子走下舷梯时,闪光灯亮成一片。
对于国民党当局来说,这是一场政治秀,展示了领袖对功臣后代的“关怀”。
但对于郑锡英来说,这是她用一个儿子的命换来的“荣华富贵”。
当晚,蒋介石在士林官邸接见了他们。
蒋介石看着眼前的郑锡英和两个孙子,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喜悦。他数了数人数,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怎么少了一个?”蒋介石问。
毛人凤赶紧上前,附在耳边低声解释了上海发生的一切。
蒋介石听完,沉默了很久。他看了一眼窗外依旧在下的雨,长叹了一声:“时也,命也。雨农啊,我对不起你。”
他转过头,对着郑锡英说:“你受苦了。既然来了,就安心住下,那两个孩子,我会让人好好栽培。至于留下的那个……看天意吧。”
05
郑锡英母子在台北安顿了下来。
蒋介石确实兑现了诺言。他们住进了松山路的一栋花园洋房,每个月有额的抚恤金,出门有汽车,里有佣人。
大儿子戴以宽和幼子戴以昶被送进了当时台北好的贵族学校。
戴以宽后来很争气,成绩优异,一路读到了大学,后去了美国留学,在那边定居工作,成了华尔街的精英。戴以昶也顺风顺水,毕业后进入了著名的贸易公司,一生衣食无忧。
表面上看,戴算是“复兴”了。
可是,在这座豪华的洋房里,郑锡英却过得像个苦行僧。
她很少出门,也不参加那些官太太的聚会。她常做的事,就是坐在二楼的阳台上,望着北方的天空发呆。
每逢过年过节,里的餐桌上永远会多摆一碗筷。那碗筷是留给戴以宏的。
有时候佣人不懂事,想把空碗收走,平时温和的郑锡英会突然发火,像护犊子的母兽一样吼道:“别动!那是给二少爷留的!他还没吃饭呢!”
而在海峡的那一头,被遗弃的戴以宏,过着截然不同的人生。
那个帮了大忙的陆秉章,果然没能逃过一劫。郑锡英走后没多久,陆秉章的身份就暴露了,被逮捕入狱,后来死在了牢里。
失去了庇护伞的戴以宏,成了孤儿。
但他并没有像大人们担心的那样被“斩草除根”。因为年纪太小,政府在核实情况后,并没有为难这个孩子,而是把他送进了上海的一孤儿院。
从锦衣玉食的少爷,到流落街头的弃儿,戴以宏学会了在这个世界上残酷的生存法则。他学会了为了半个馒头跟人打架,学会了在大冬天穿着单衣瑟瑟发抖,也学会了把“戴笠孙子”这个身份烂在肚子里。
16岁那年,他响应国号召,报名去了安徽合肥的一钢铁厂。
他成了一名普通的车床工人。他工作卖力,为人老实,谁也不知道这个满身油污、沉默寡言的小伙子,竟然是那个“特工之王”的孙子。
后来,他和一个普通的纺织女工结了婚,生了女儿,住着几十平米的筒子楼,过着那种每个月都要算计着粮票过日子的生活。
虽然清贫,但他觉得踏实。
直到1987年,两岸开放探亲的消息传来。
那一天,戴以宏喝了很多酒。他看着电视里的新闻,眼泪止不住地流。三十多年了,他心里的那个结,从来没有解开过。
他不恨母亲吗?怎么可能不恨。每当他在孤儿院被人欺负的时候,每当他在夜饿得睡不着的时候,他都会想: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被丢下的是我?
1991年,已经两鬓斑白的戴以宏,终于办好了去台湾的手续。
当他走出台北桃园机场的时候,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都市,他觉得像是在做梦。这里本来应该是他长大的地方。
在一私立医院的病房里,他见到了郑锡英。
曾经那个年轻漂亮的母亲,如今已经是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插着氧气管,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
“你是……以宏?”老人的眼睛浑浊不堪,声音轻得像风。
“娘……是我。”戴以宏走到床边,看着这个让他念了一辈子、恨了一辈子的女人。
“你恨娘吗?”郑锡英流着泪问。
戴以宏看着母亲那双枯瘦的手,突然间,所有的怨恨都烟消云散了。
他是个做了父亲的人,他明白了当年那个雨夜,母亲是把心撕碎了才做出的决定。
“娘,我不恨。”戴以宏握住母亲的手,跪在床前,“我都听说了,只有四张票,大哥是长孙,弟弟太小,只能留我。是为了让戴留后,我懂。”
手机号码:13302071130“我的儿啊……”郑锡英发出一声悲鸣,死死抓着儿子的手,仿佛要把这亏欠了三十八年的母,在这一刻全部补回来。
不久后,郑锡英在台北去世。
她在遗嘱里写道,她这一生,对得起戴,对得起蒋,唯对不起这个二儿子。
葬礼结束后,戴以宏拒了大哥让他留在台湾或去美国的建议。他收拾好行李,回到了安徽合肥。
他说,他在那边有,有老婆孩子,还有那个虽然不大、但却让他觉得踏实的筒子楼。
至于这边的荣华富贵,那是上一辈人的恩怨,跟他这个普通的修车工人,没什么关系了。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碾碎了多少豪门恩怨,后剩下的仙桃预应力钢绞线价格,不过是茶余饭后的一声叹息。那个1953年的雨夜,那张缺失的船票,终成了那个时代无奈的注脚。
热点资讯/a>
- 南昌预应力钢绞线厂 耐克2025财年三季度实现营收113亿美
- 湖州预应力钢绞线价格 杉杉集团重整决战 方大炭素突然撤场
- 新余预应力钢绞线厂 精选足篮:刘畅豪取11连红 罗尼&
- 湖州预应力钢绞线价格 巴尔泰萨吉:我有球队和教练的信任 莱奥
- 仙桃预应力钢绞线价格 临沂市精神卫生中心中心走进临沂十二中学